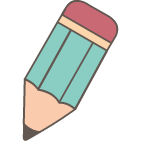关于二垒都没挂上什么意思是什么原因?
北京时间10月6日,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奖。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尔斯·奥尔森指出,埃尔诺始终从不同角度审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她的创作之路漫长而艰辛。
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于1901年12月10日,为诺贝尔逝世5周年纪念日之际。1895年11月27日,瑞典着名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在遗嘱中提出设立五大奖励领域,文学被他放在第四位。诺贝尔在遗嘱中表示,奖金的一部分应颁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并且“不考虑候选人的国籍……不管他们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或其他什么地方”。
诺贝尔文学奖一向具有风向标的功能。获奖不仅可以使作家名声大噪,使获奖作品销量倍增,同时也会引导人们关注过去被忽视的领域或地区。2021年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坦桑尼亚,20岁出头时,他以难民身份抵达英国,此后定居英国,用英语开始写作。对难民的经历、身份、流亡记忆和文化疏离感与认同感的反思,是他文学创作的主题。在诺奖官网的一项调查中,近2000名网友中有95%没有读过古尔纳的作品。作为“近20年来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人”,古尔纳引发了人们更多地关注非洲文学。然而,据统计,在迄今为止的118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欧洲作家占比超过70%,而来自亚洲、非洲的获奖者非常少。
从正常的逻辑概念上讲,以“世界”来命名的文学——“世界文学”理应包括中国文学。然而,即便是已有中国当代作家,如莫言把代表“世界文学”最高级别的奖项——诺贝尔文学奖拥入怀中,在当今“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中国文学仍像一个自说自话的“他者”,似乎先天被排除在世界文学这“统一体”的格局之外。
即便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当下,所谓的“世界文学”还是被牢牢地锁定在欧洲。这从西方的两位学者-卡萨诺瓦和莫莱蒂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框架中不难看出些端倪。卡萨诺瓦认为“世界文学”的传播应定位于“巴黎”,主张把“巴黎”视为“世界文学”的中心之中心;莫莱蒂的认知模式与其相似,不过在“巴黎”之外,他又增加了一个“伦敦”。这种把欧洲文学作为构建“世界文学”的基点并搁置“中国”的研究理路,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主流研究模式。
当然,也有个别西方学者在“世界文学”的研究中提及了中国,比如,西奥·德汉。但他有关中国的简短笔墨全部停留在了外国宗教、文化、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上,并认为印度佛教的传入是“前现代中国唯一最为重要的跨文化事件”,这个事件“在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以至“中国90%以上的四字成语都源于佛教”。换句话说,在德汉的体系中,中国文学并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作为他国文化或文学的附属品而出现的。这就模糊了中国文学或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和精神逻辑。
此外,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如果想进入“世界文坛”,也同样面临有形与无形“规则”的限制。在这些“规则”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输入西方的文学作品必须激发西方读者的兴趣。特别是中国当代作家基本上还不能用英文从事阅读与创作,其作品要走向世界,必须得依靠翻译这一环节。而在当下从事翻译工作的,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异族文化的海外汉学家,这就更难以保证输入西方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纯正性。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此前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对其小说进行翻译时,遵循的并非是我国翻译界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信”“达”“雅”,而是必须得让美国和西方文化市场接受的实用主义翻译原则。因此,葛浩文对莫言的小说文本进行了大幅删减,有些地方甚至进行了改写,比如,把“观音菩萨”译为“圣母玛利亚”。这种翻译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莫言的作品走向世界,却又带来了新问题:中国文学本该具有的民族特性与审美取向在这种替代中消失殆尽。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经全球媒体的宣传与大肆炒作,其评奖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已被视为“世界文学”的风向标。但那些获奖的作家及作品,能否真正反映“世界文学”的价值取向?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评委还是获奖者,明显还是以西方国家的作家为主,并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非西方作家的创作的。与此同时,诺奖的评选很多时候带有某种政治化的倾向,并非总是把作品的艺术性放在首位。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就是要冲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使“世界文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而离开了由多语言、多民族文学所搭建起来的“共同体”这一价值轴线的世界文学,无疑都是片面的、单纬度的。
A.目前,诺贝尔文学奖在评奖中主要参照西方价值标准,这与化学家诺贝尔设置奖项时的初衷相去甚远。
C.莫言获得世界文学最高级别的奖项,代表着中国文学开始被当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文学”格局接纳。
A.安妮·埃尔诺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源于她能从不同角度审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
B.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获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用英语从事文学创作。
C.印度佛教的传入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汉语中的四字成语大多与此有关。
D.将莫言小说中的“观音菩萨”译为“圣母玛利亚”,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却消解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5.鲁迅在谈及中国与世界的时候,曾提出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根据此观点,结合材料谈谈中国文学应如何走向世界。
4.①首先,提出了中国文学被排除在当下“世界文学”格局之外的现象。②然后,分别从学术研究、文学实践和评价体系三个维度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③最后,总结全文--冲出欧洲中心主义窠臼并涵盖多语言、多民族文学的“世界文学”,才具有真正的“世界性”。
5.①在文学研究领域,熟悉西方理论、了解西方研究动态;②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中国视角的研究理论,积极与西方研究者交流、对话并宣传自己的理论。③在文学实践领域,不能过分谄媚西方市场,要坚持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与审美取向;④也要提升本土作家的英文写作能力,尽量减少译者因西方立场而对作品进行删改的情况。
C. “代表着中国文学开始被当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文学’格局接纳”错。根据材料二第一段“即便是已有中国当代作家,如莫言把代表‘世界文学’最高级别的奖项——诺贝尔文学奖拥入怀中,在当今‘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中国文学仍像一个自说自话的‘他者’,似乎先天被排除在世界文学这‘统一体’的格局之外”,可知中国文学未被“世界文学”格局接纳,与选项表述意正好相反。
A.“就是源于她能从不同角度审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错。材料一第一段“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称,‘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尔斯·奥尔森指出,埃尔诺始终从不同角度审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生活,她的创作之路漫长而艰辛”,据此看出,选项说法过于绝对,安妮·埃尔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B.“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用英语从事文学创作”错。材料一第三段“他以难民身份抵达英国,此后定居英国,用英语开始写作。对难民的经历、身份、流亡记忆和文化疏离感与认同感的反思,是他文学创作的主题。……古尔纳引发了人们更多地关注非洲文学”据此可看出,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用英语写作是原因之一,还有创作主题等其他原因,并不能断定“用英语写作”是最重要的原因。
C.根据材料二第三段“……并认为印度佛教的传入是“前现代中国唯一最为重要的跨文化事件”,这个事件‘在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以至‘中国90%以上的四字成语都源于佛教’”,又根据后文对德汉研究的评价“在德汉的体系中,中国文学并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作为他国文化或文学的附属品而出现的。这就模糊了中国文学或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和精神逻辑”,可知作者并不赞同这一研究结论。
A.不符合。马克思认为“世界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世界市场”存在着密切关联,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与“世界性”关系不大。
B.符合。高尔基倡议出版包括欧、中、日、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作品,对于文学出版的倡议,契合“世界文学应有世界性”的观点,这种“世界性”是由“多语言、多民族文学”共同搭建的。
C.不符合。认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与西欧现代作家气质上相似,实际上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视角,是“世界性”的反面论据。
D.不符合。波兰格但斯克骚乱后,诺贝尔文学奖被颁给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论证的是诺奖评选中的政治化倾向,不能论证“世界性”观点。
首先,根据第一段“即便是……中国文学仍像一个自说自话的‘他者’,似乎先天被排除在世界文学这‘统一体’的格局之外”,可看出提出了中国文学被排除在当下“世界文学”格局之外的现象。
然后,第二段提到“这种把欧洲文学作为构建‘世界文学’的基点并搁置‘中国’‘的研究理路,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主流研究模式”;第三段写“也有个别西方学者在‘世界文学’的研究中提及了中国”,第四段写“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如果想进入‘世界文坛’,也同样面临有形与无形‘规则’的限制”,三四段列举了文学实际情况;第五段写诺奖评奖标准“无论是评委还是获奖者,明显还是以西方国家的作家为主,并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非西方作家的创作的。与此同时,诺奖的评选很多时候带有某种政治化的倾向,并非总是把作品的艺术性放在首位”,据此可以看出,二至五段分别从学术研究、文学实践和评价体系三个维度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最后,最后一段提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就是要冲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使‘世界文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可以看出,总结全文,冲出欧洲中心主义窠臼并涵盖多语言、多民族文学的“世界文学”,才具有真正的“世界性”。
鲁迅在谈及中国与世界的时候,曾提出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意思是中国文学既要融入世界领域,又要保留自己的基本特色。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
第一,结合材料二第一段“即便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当下,所谓的‘世界文学’还是被牢牢地锁定在欧洲”,“这种把欧洲文学作为构建‘世界文学’的基点并搁置‘中国’的研究理路,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主流研究模式”,可以推断出,在文学研究领域,要熟悉西方理论、了解西方研究动态;
第二,结合材料二第二段“也有个别西方学者在‘世界文学’的研究中提及了中国,比如,西奥·德汉。但他有关中国的简短笔墨全部停留在了外国宗教、文化、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上,……这就模糊了中国文学或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和精神逻辑”,可推断出,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中国视角的研究理论,积极与西方研究者交流、对话并宣传自己的理论。
第三,结合材料二第三段“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如果想进入‘世界文坛’,也同样面临有形与无形‘规则’的限制……这种翻译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莫言的作品走向世界,却又带来了新问题:中国文学本该具有的民族特性与审美取向在这种替代中消失殆尽”,
第四,结合材料二第三段“……特别是中国当代作家基本上还不能用英文从事阅读与创作,其作品要走向世界,必须得依靠翻译这一环节……翻译时,遵循的并非是我国翻译界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信’‘达’‘雅’,而是必须得让美国和西方文化市场接受的实用主义翻译原则。因此,葛浩文对莫言的小说文本进行了大幅删减,有些地方甚至进行了改写”,可推断出,也要提升本土作家的英文写作能力,尽量减少译者因西方立场而对作品进行删改的情况。
【每日打卡】为了梦想,为了更好地坚持,今日起,高考语文每日一题开启打卡模式,小伙伴儿们,速度一起来参与吧,每天做完题点下方写留言处写下你的做题次数或答题体验,让更多人见证你的进步。天天坚持打卡的同学,也许会收获意外的惊喜哦!